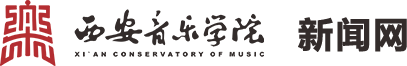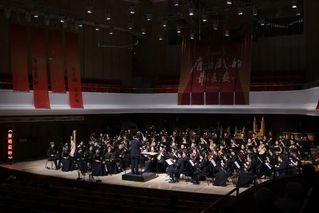工作十余年,我们常谈做教师的感受,也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磨合师生关系。又到教师节,更是想起我的老师——在西安音乐学院从教三十余年的罗艺峰教授。拿起手机,感性的问出一直以来对老师学术发展、人生经历的疑问,带来了老师的回忆,耳边也再次在毕业多年后听到了生动温暖的话语,也让我从老师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不懈的努力,师者的仁心,温暖的扶助……也给我启示与思考。
柳琳(后文简写为柳):老师,您的学术风格一直是突出多元的,这与您的人生经历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学无常师——从演奏到作曲
罗艺峰(后文简写为罗):说起来呢,我的学术道路,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也很难复制。大家都知道,我是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因此我的学术道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的学术思维、学术领域、学术方法、学术理念,也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简单的讲一讲我的经历,我在家乡的一个歌舞团工作了将近十五年,在乐队里坐了十年——主要是吹小号,演出过很多很多的节目,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又从事作曲和指挥。在十多年的音乐工作当中,由于工作的需要,完全靠自学完成了作曲四大件的学习和大量的总谱分析,文革后期我创作了一部歌剧叫做《追鱼》,它早先是一部电影,后来被我们这个歌舞团改编成了歌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歌剧的演出活动沿着长江,一直演到上海。我的习惯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图书馆和旧书店,上海的福州路,过去是旧书店云集的地方,在那里我花很少的钱买到了前苏联斯波索宾的《和声学》、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管弦乐法》,还有其他乐器学以及乐理方面的书。没有条件上大学的时代,我的知识完全是靠自学的,这培养了我很强的自学能力,也影响了我后来的道路,我从一个演奏员成长为能够写作大型作品的作曲者,能够耐下心来学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也源自于我的经历,我在我们中学的图书馆练就了读书的功夫,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守图书馆,借这个机会,我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的各种各样的书,包括艺术类的书。我的学术训练呢,其实用得上古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学无常师”,常师就是恆常之师、唯一的老师,我没有恆常的唯一的老师,也就是见什么学什么,见人就学。因此也就养成了我读书思考的这么一个习惯。
说起来我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小泽征尔率领波斯顿交响乐团到北京,每个省只能选两个人去听这场音乐会,且参加随后的指挥讲习班,我有幸被江西省选上。那场《贝九》的演出看得我热血沸腾,那时候我立定了一个理想就是做个指挥,不过最终没有做成,而成为了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教书匠。
常遇名师——从作曲到音乐学
大概是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招收文革后的第一届作曲研究生。我那个时候特别痴迷复调,所以就读了一些复调方面的书、写了一些作业、作品,报考了上音的陈铭志老师的硕士研究生,陈铭志老师是我们国家老一辈的复调专家。在几十个全国的报考人当中呢,我很有幸进入了最后的复试。当时我在江西工作,报考上音的研究生,没有学历,也没有任何学术背景,当时并没有考上。但很多年后一次开会,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陈老师说“原来你就是罗艺峰,我们找了你很久,现在总算见到了……”多年过去,他还记得我当时的作品还不错,令我倍感老师的温暖。
到了八零年代,我还是非常的想往心中的圣地——中央音乐学院。那个时候也没有学历的意识,也没有条件报考,于是我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旁听了两年的作曲课程。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作曲班有六、七个人,我是第八个。其实这几个人都是后来的“大腕儿”,比方说像谭盾、瞿小松、叶小纲、陈怡、周龙、朱世瑞以及后来写小说《你别无选择》出了名的刘索拉等等。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都非常非常的棒,象于苏贤老师、段平泰老师、张文纲老师等,他们不仅仅是老一辈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教学上的认真、学术上的严谨,很了不起!学院那个时候对于我这个旁听生呢,给予了全副的关照,没有学费,而且所有的讲义、谱例、改题都是由学校安排,我做完了所有的和声、复调、配器、作品分析作业。那两年,我接受了专业训练,却没有过学历这个“名分”。
我呢,很少跟人讲这些事情,你可能也都不了解。但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浓厚的音乐学术氛围下,我慢慢的转向了音乐学理论,常常去听音乐学系的课,由于我中学开始就有的强烈的哲学兴趣,后来我就转到了音乐学系,在于润洋[1]老师的安排下,我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何乾三[2]教授。她是我的恩师,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老师,跟随她,我进入了音乐美学的领域。虽然我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正式的学生,但那是我出发的地方,于润洋老师曾经在一个大雪的冬天把我叫到他家去,那时候他住在南线阁,跟我畅谈音乐美学的问题,当他阅读完我的第一篇音乐美学论文《论音乐中的“增熵”现象》,他跟我说:“小罗,你真的要进入音乐美学么?”我说:“是的”,他说:“你知道这是苦海无边的事业吗?”我说:“我愿意!”。从此,我就跳进了音乐美学学科这个“苦海”来了,这一跳下去就是三十多年。可以说我的第一篇音乐美学论文就是在于润洋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在他家里完成的,后来文章投稿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学报《音乐艺术》,编辑就把文章转给了钱仁康[3]先生。钱先生,也是当时我也非常崇拜的一个音乐学界的老前辈,他在给我这个来往的信件中讨论我的论文中的“增熵现象”,他的知识非常广博,他提出还有一条路线叫做“减熵现象”,在我文章中没有涉及,并指导我进行了修改。这篇文章呢被很多人认为非常难懂,于润洋先生当时也曾跟我说:“小罗啊,你的第一篇文章学术起步就这么高,那你以后怎么走呢?”我觉得是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和警示,提醒我时刻不能放松。钱先生、于先生他们的学术智慧,对我来说是一个榜样,他们两位亦可以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
在中央音乐学院期间,我跟蔡仲德先生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虽然我们两个年龄相差不大,他年长一些,学术上也比我好。我那个时候啊,可是一个完全的“崇洋媚外”派啊,对中国的东西知之甚少,只是到了四十五岁以后,逐渐的转向中国,有许多的现实问题来刺激我思考音乐的问题,学术的问题、历史的问题、美学的问题、创作的问题等等。
可以说,在我学术起步的道路上,总是能够遇到一些名师-恩师,他们的道德文章、精神气质和不懈追求一直影响着我,这是我的幸运啊。
恩师引路——从江西到西安
柳:在您的工作经历中,从江西来到西安,目前更是把研究交流的视野放在更大的范围里。在这几次变化中,您如何思考的呢?
罗:我之前生活在江西南昌,这个地方被人称为是“吴头楚尾”,就是吴文化的头、楚文化的尾,更有人称这里是“文化的洼地,交通的盲肠”。在文化上缺乏特色。而且在艺术教育上不是很发达,江西没有音乐学院,我就特别想往有音乐学院的地方。当时西音的刘大冬院长经过高士杰老师的介绍,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由那时学报的负责人张文立老师亲自带着这封信到南昌找我,邀请我到西安来工作。我当时非常的感动,那时候的我什么也不是:没有头衔、没有职称,甚至没有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可是呢,人家院长来请我,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可是最有趣的是,在要走的时候,单位以“流失人才”(把调动的事儿)在那儿扣了一年多,临行的时候,当地的报纸还是发了一篇通讯叫做《西去长安不回头》。
当时,我跟梅老师(妻子)带着只有三岁的孩子,举家搬迁到了西安。在这里已经三十年整,我深深的爱上这个城市,爱上这里的文化,爱上了西安音乐学院,三十年甚至改造了我的胃,常常会像陕西人一样想吃面和羊肉泡。虽然我不是西音毕业的校友,但我在这里贡献了我三十年的青春、三十年的人生,这里是我的第二个福地。西音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刘大冬[4]院长,一个是高士杰[5]老师。刘大冬院长的诚恳、睿智和执着、他待人的方式使我深深的感动,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来对了。我下火车到这里住的是北楼正对走廊的那一间琴房,而后学校给我租了一间隔壁新加坡村老百姓的民房,我们全家住在那儿。那非常冷,冬天也没有暖气,冬天那房子里的尿盆儿都结了冰啊。但是呢,学校对我的肯定让我非常温暖,让我喜欢这个地方。刘院长当然是我的恩师,由于我学习作曲和指挥的经历,他的排练,我经常去听,同时,刘大冬院长的为人、治校、治学的智慧,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位恩师就是高士杰老师。他整整大我20岁,我到达西安的第一顿饭是在高老师家里吃的。第二顿饭是刘老师带我吃的羊肉泡馍,刘老师看我吃的可香了,就说,“好啦,我相信你能留下来”,可见刘院长用心之深之纯。这句话我三十年来没有忘记,我应该对得起这句话。高士杰先生给我的影响,大概说来就是永不停步的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的思考。我们从来不说闲话,见面就直奔主题:“最近在看什么书?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治学态度,真的是对我影响很大,他是我的学问上的挚友。高士杰老师现在九十岁了,我真心的祝愿他长寿,直奔百年。
成为名师——求索、创新、不断转型
柳:从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到音乐思想史,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不断的求新求变?在美学、人类学、教育学、音乐思想史之间的转型与变化中,是否有着某些联系呢?
罗:在西安音乐学院,我是第一个开设美学课的。音乐美学是我的主业,大家也一般都认为我是以音乐美学为志业的。但是我因为“学无常师”,也必然带来跨学科的兴趣。所以我也就进入了音乐人类学的领域,也在音乐教育领域有所涉猎,到了五十多岁以后,进入了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
我的多学科涉猎并不是我企图或者说我妄想跟古今大人物平起平坐,而是我有这样强烈的知识兴趣。这种转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广泛的知识兴趣,这一点呢,我觉得音乐学界是应该考虑,因为音乐文化本来就是含纳多学科知识的。古今中外,从事音乐学的这些同行们的状态,和我们只限于声音的工艺结构的分析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像德国比较音乐学的早期大师们,有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学数学的,还有学哲学的、学语言学的,他们为什么成为了音乐学家呢,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的强力集团这些作曲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从事专业音乐的,他们为什么成为了作曲家呢?我们中国古代这种状态就更多了啊,后来我研究思想史,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这是古代音乐思想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些学科里有所作为。人类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兴起。但是音乐人类学国内的状态仍然非常的低迷、落后,我是起身比较早的一个,我觉得我的学术敏感还是可以的。正好这个时候呢,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的钟正山先生到西安来访。他找到了我,同我谈了去马来西亚访问的问题,于是我以此申报了我的第一个国家课题——“华南民族音乐与马来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属于国家“八.五”人文社科项目,九十年代初国家拨付了三万块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合作,到马来进行了为期一百天,覆盖其十三个州的田野工作。当时采访了很多人,也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出版了《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作为国内较全面研究马来民族和当地土著音乐的一本音乐人类学著作,这本书获得了陕西省人文社科一等奖,也受到学界好评。
在音乐美学领域,我坚持第一线的教学,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并担任了全国音乐美学协会的副会长。从事音乐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来,受到大家的肯定的评价。在音乐教育领域,其实我是长期关注的,后来也招了研究生。
我认为美学要研究人类的感性实践,而感性实践又是人类的文化行为,因此跟人类学有关,而文化传统的延续或者是研究往往又跟教育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有深刻关联的。但是最终归根结底,人是思想的动物,人为什么要有音乐?为什么要去审美?为什么有音乐行为的差异?为什么有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行为的差异?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个这方面呢,只有中国音乐美学史而没有中国音乐思想史,这个给我很大的刺激。
你到书店去,你能看见有中国文学思想史、美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甚至还有财会思想史,可是居然没有音乐思想史!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非常丰富、影响十分巨大,没有音乐思想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欠缺。我跟西北大学的张岂之[6]先生(他是中国思想史这个专业的一个大专家啊),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事儿你得做啊!”我就跟他讲:“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如果只研究‘礼’不研究‘乐’,就是只有一条腿在走路啊。”他回应说:“我们不懂啊,应该你们来做!”我说:“好。”但是这一句“好”就耗了我十年。《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的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还获得了陕西省人文社科研究一等奖,这是我第二次获得省里一等奖了。前不久在学校召开的“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高端论坛”是对这个学科非常重要和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学校张立杰书记看到了音乐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亲自到场讲话祝贺。音乐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目前我培养了五、六个这个方向的博士生,我的一位硕士生还考到张岂之先生门下读完博士了,现在专攻秦汉礼乐制度研究,但是这个队伍仍然弱小,光靠我一个人不行。我在书后的“跋语”中曾经说到,希望能对得起先人,对得起传统,不能因为自己的浅薄误读了古人,因为这个学科非常难,要读的古书很多,要了解的知识很深,绝非一蹴而就的事。
可以说,知识兴趣、学术追求和现实思考,是我在多学科领域里探索的原因。
不忘恩师——我与恩师的相遇
向老师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老师在学术经历中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有趣故事呢?老师声音饱含笑意的告诉我“有一个呢,就是我从事了一辈子音乐工作,却被人认为不懂音乐。最近这一两年我常常听到这些对我的质疑,有人认为呢,看我的文字觉得我是学中文的;有人看了我的思想史著作呢,又觉得我像是学历史的;有人看了我的美学文章呢,又觉得我是搞哲学的。他们质疑说:罗老师是搞音乐的吗?他懂音乐吗啊?被人说成是不懂音乐。虽说人家是不了解,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可乐的一件事儿吧!”
想想当年,我也是因为文字优美才被吸引的学生啊。
记忆被带回2004年,我借着帮学长给罗老师送一套复刻音响资料的机会,怯生生的敲开罗老师的家门,他正同女儿和两名学长在家午餐。我憋红了脸说:“老师好。我是音乐学系的本科生,我是专业第一名,我想跟您学习美学,我并不知道美学是什么,而我觉得您的文章写得好,我想学。”老师笑了笑说,“你是不是第一名有什么关系,即便是学习不好的孩子,能跟着我学成第一名,才是我想要的学生。”在七年的学业进程中,我不免感性,也不免局限于抽象思维能力的不足,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高质量的完成了学术性较强的本科毕业论文,并懂得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去了解古人”,饱含情感的完成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
十年来,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我也常常感念于同老师的相遇那日,相信即便是不好的孩子也要有优秀的机会。我也学着老师的样子,拼命的获取音乐之外的知识,拼命的学习与音乐知识相关的姊妹艺术,努力了解当下青年人喜欢的文化现象和知识,用生动的事例,完整的语言表达,带给他们更具吸引力,通俗易懂,记忆深刻的课堂经历。那些平日里在课堂上并不出众的孩子,兴奋的拿着结合了他们兴趣和音乐学术知识的毕业论文,告诉我说,与我相遇是福气的时候,我想说,这正是我的老师给予我的恩。
罗老师的人生经历成为他积累学术成就的宝库,而身为老师的学生,在此次交谈中我也深有感悟:
知识上学无常师,让我们学会用多个角度看待学术世界。
学业中莫记得失,让我们能够更充分的获取知识,直面自己的学业需求。
学术中求新求变,让我们能够更完整的看待学科关系,寻找学术突破。
生活中常记师恩,让我们记得来时的路,看清当下的时光,寻找更好的自我。
[1]于润洋,男,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我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何乾三,女,是我国著名的音乐美学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初期筹建者之一,为我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3]钱仁康,男,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北平师范学院、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苏南文教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博导,中国第一位音乐学博士生导师。
[4]刘大冬,男,中国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教育家,曾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
[5]高士杰,男,音乐学家,音乐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8年起任教于西安音乐学院,曾任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责任编辑: